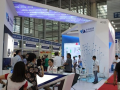人工智能(Artificial Intelligence,縮寫(xiě)為AI)不只涌現(xiàn)在《終結(jié)者》之類的科幻片子當(dāng)中,也開(kāi)端走進(jìn)我們的實(shí)際生涯。好比,綜藝節(jié)目《最壯大腦》中,機(jī)械人“小度”在圖象辨認(rèn)等方面完勝人類選手;谷歌旗下公司開(kāi)辟的人工智能法式AlphaGo克服了圍棋世界冠軍。就連人類引認(rèn)為傲的文藝創(chuàng)作,也開(kāi)端遭受人工智能的挑釁。日前,就在《中國(guó)詩(shī)詞年夜會(huì)》熱播的時(shí)刻,清華年夜學(xué)語(yǔ)音與說(shuō)話試驗(yàn)中間(CSLT)作詩(shī)機(jī)械人“薇薇”經(jīng)由過(guò)程了“圖靈測(cè)試”(“圖靈測(cè)試”是有名迷信家圖靈在1950年提出的一個(gè)不雅點(diǎn),行將人與機(jī)械離隔后,假如有30%以上的機(jī)械行動(dòng)被人誤解為是“人”而不是“機(jī)械”所為,則機(jī)械應(yīng)被視為具有智能。)機(jī)械人“薇薇”創(chuàng)作的詩(shī)歌令社科院的唐詩(shī)專家沒(méi)法分辯,有31%的作品被以為是人寫(xiě)的。另外,“機(jī)械人寫(xiě)小說(shuō)”“電腦作曲”的報(bào)導(dǎo)也開(kāi)端見(jiàn)諸報(bào)端。 文藝創(chuàng)作,是經(jīng)由過(guò)程人腦停止的一種與情緒、知覺(jué)、記憶與思想相干的龐雜的精力運(yùn)動(dòng),這本是人類的自滿。人工智能何故可以或許攻進(jìn)這一人類獨(dú)有的領(lǐng)地?面對(duì)人工智能,人類傳統(tǒng)的文藝創(chuàng)作又會(huì)見(jiàn)臨如何的挑釁? 機(jī)械人“薇薇”開(kāi)啟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詩(shī)歌寫(xiě)作形式 運(yùn)轉(zhuǎn)法式來(lái)寫(xiě)作和法式自己一樣陳舊。世界上第一臺(tái)可運(yùn)轉(zhuǎn)法式的盤算機(jī)運(yùn)轉(zhuǎn)的第一個(gè)法式,就是由迷信家克里斯托弗·斯特雷奇(Christopher Strachey)編寫(xiě)的情詩(shī)法式。該法式會(huì)抓取一些甜美的辭匯,聯(lián)綴成浪漫的戀愛(ài)詩(shī)。好比“親愛(ài)的,你是我深深的愛(ài)戀”之類。 機(jī)械人“薇薇”關(guān)于詩(shī)歌的懂得,和它1948年的老祖宗類似。先來(lái)看看這首《春雪》:飛花輕灑雪欺紅/雨后春風(fēng)細(xì)柳工/一夜東君無(wú)窮恨/不知何處覓青松。這首詩(shī)一看就是機(jī)械人愚笨的模擬,只要完整不懂詩(shī)的人會(huì)以為這是“詩(shī)人”寫(xiě)的。不說(shuō)格律上的請(qǐng)求,就以文句揣摸,第一句說(shuō)下雪,第二句又說(shuō)下雨,究竟是雪照樣雨?三四句除用了“東君”、“青松”之類罕見(jiàn)的字眼外,內(nèi)容不知所云,完整在凌亂堆砌。 必需說(shuō),有的詩(shī)斷定的難度要年夜一點(diǎn),好比這一首《落花》:紅濕胭艷逐零蓬/一片春風(fēng)細(xì)雨濛/燕子不知無(wú)處去/東流猶有杜鵑聲。這一首的鑒別須要斟酌,但只需略加思慮,“細(xì)雨濛”之種別扭的用法照樣可以被辨認(rèn)出的。同時(shí)從詩(shī)歌的內(nèi)涵節(jié)拍看,這首詩(shī)不克不及說(shuō)必定是機(jī)械人寫(xiě)的,但節(jié)拍比擬蹩腳,頭兩句帶有二人轉(zhuǎn)的韻律。 由這一類詩(shī)歌來(lái)剖析,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上,人工智能在模擬甚么?人工智能的寫(xiě)作實(shí)質(zhì)上是一種“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寫(xiě)作”,其關(guān)于文學(xué)的模擬高度依附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,越是海量數(shù)據(jù),越有助于人工智能的進(jìn)修。好比,AlphaGo進(jìn)修了三萬(wàn)萬(wàn)步的人類棋譜。“薇薇”這類寫(xiě)詩(shī)的人工智能法式,不曉得進(jìn)修過(guò)量少首古詩(shī),估量是《全唐詩(shī)》五萬(wàn)首的幾何倍數(shù)之上,故而可以在外面上,停止一些有模有樣的模擬。 不只是詩(shī)歌寫(xiě)作,人工智能在其他范疇的寫(xiě)作,也都是“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”寫(xiě)作。幾年前美聯(lián)社、雅虎網(wǎng)、福布斯網(wǎng)就應(yīng)用人工智能依托消息模板生成體育類、財(cái)經(jīng)類消息稿。2008年,聽(tīng)說(shuō)是機(jī)械人寫(xiě)的長(zhǎng)篇小說(shuō)《真愛(ài)》在俄羅斯出書(shū),這本320頁(yè)的小說(shuō)電腦只寫(xiě)了三天——在有幾千本文學(xué)名著作為數(shù)據(jù)庫(kù)的基本之上。 關(guān)于科技入侵文學(xué)的憂愁幾回再三顯現(xiàn) 不像圍棋是有輸贏關(guān)系的,在某種水平上可以被量化,詩(shī)歌所展示的說(shuō)話的幽美與豐碩的人類心坎世界,永久沒(méi)法被量化、被尺度化。人工智能在“瀏覽”上可以遠(yuǎn)遠(yuǎn)超越一切詩(shī)人,可以或許辨認(rèn)出哪些詞是高頻的,可以依照根本的詩(shī)歌規(guī)矩組合出一首詩(shī),但這類組合不是創(chuàng)作。 在這個(gè)意義上,沒(méi)法差別的,是蹩腳的作品與機(jī)械人寫(xiě)的作品。假如把杜甫的詩(shī)和機(jī)械人寫(xiě)的詩(shī)混在一路,確定輕易辨別。 是以,就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而言,人工智能將來(lái)有能夠在編劇或收集文學(xué)方面有所沖破,究竟除一小部門出色的作品外,不管腳本創(chuàng)作照樣收集文學(xué),比擬依附尺度化的情節(jié)形式與詞語(yǔ)搭配。而文學(xué)作品的形式化水平越強(qiáng),越有能夠人工智能化。歸納綜合地說(shuō),人工智能關(guān)于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的代替,今朝所能瞻望到的最高造詣,是代替淺顯文學(xué),有一天也許是電腦本身來(lái)打字,上傳一部及格的收集文學(xué)作品到網(wǎng)站上。 拉長(zhǎng)汗青視野來(lái)看,每當(dāng)技巧變更有偉大沖破時(shí),關(guān)于科技入侵文學(xué)的憂愁就幾回再三顯現(xiàn)。本雅明在1936年完成的《機(jī)械復(fù)制時(shí)期的藝術(shù)作品》一文中,就表達(dá)過(guò)攝影、片子涌現(xiàn)后藝術(shù)作品“光韻”滅亡的遺憾,而隨同著播送、電視、收集的涌現(xiàn),文學(xué)這門陳舊的藝術(shù)一次次被宣判逝世亡。我們不用對(duì)此消極。文學(xué)實(shí)際年夜家錢谷融師長(zhǎng)教師在20世紀(jì)50年月就提出過(guò)“文學(xué)是人學(xué)”,文學(xué)的龐雜一直對(duì)應(yīng)于人心的深?yuàn)W,只需魂魄沒(méi)有干涸,文學(xué)這朵藝術(shù)之花會(huì)永開(kāi)不敗。 人道是永久沒(méi)法替換的部門 在明天評(píng)論辯論人工智能與文藝的關(guān)系,筆者認(rèn)為真正擔(dān)憂的不是人工智能開(kāi)端文藝創(chuàng)作,而是我們關(guān)于文藝的懂得趨勢(shì)人工智能化。某種水平上,值適合心的是反向人工智能,即人道的智能化,不是機(jī)械人釀成了我們,而是我們釀成了機(jī)械人。好比上文所引的機(jī)械人詩(shī)歌,假如有較好的詩(shī)歌教養(yǎng)其實(shí)不難辨認(rèn),但在各類偽托李白藏頭詩(shī)的口水詩(shī)都可以在收集下流行的明天,筆者擔(dān)憂愈來(lái)愈多的人將沒(méi)法斷定一首機(jī)械人詩(shī)歌和一首好詩(shī)的差距。 究竟,人工智能不是簡(jiǎn)略的“對(duì)象”,人工智能和古代社會(huì)有高度的同構(gòu)性,實(shí)質(zhì)上都是高度感性化的產(chǎn)品。以感性為焦點(diǎn)邏輯的古代社會(huì),將人道想象為“經(jīng)濟(jì)人”或“感性人”,趨利避害,以本身好處的最年夜化為目標(biāo);而人工智能所設(shè)定的“人”,可以算作是一個(gè)感性蓬勃、情緒淡薄的人,兩者的人道想象有類似的地方。 這類“感性人”與本錢高速運(yùn)轉(zhuǎn)的時(shí)期相婚配,辦事于利潤(rùn)的最年夜化。我們曉得人工智能高速成長(zhǎng)的面前,是本錢的邏輯,好比機(jī)械人家當(dāng)蔚然隆盛的一個(gè)重要緣由,就是下降人力本錢,富士康公司在2016年曾經(jīng)應(yīng)用機(jī)械人將昆山工場(chǎng)的工人人數(shù)從11萬(wàn)下降到6萬(wàn)。可以假想,假定機(jī)械人技巧更加成熟,那末剩下的工人崗?fù)ひ惨话l(fā)千鈞。假如從本錢的視角動(dòng)身,最幻想的人就是流水線上的人,或許更直接地說(shuō),是流水線上的機(jī)械人。 這再一次回到英國(guó)粹者查爾斯·珀西·斯諾在有名的《兩種文明》中提出的“迷信”與“人文”之爭(zhēng)。明天的我們注目著人工智能,或許就是在注目著將來(lái)的本身,我們必需小心迷信關(guān)于人文的步步蠶食。今朝似乎是機(jī)械存在于人類的運(yùn)轉(zhuǎn)中,但或許換一個(gè)角度,人類不外是存在于機(jī)械的運(yùn)轉(zhuǎn)中,就像卓別林的片子《摩頓時(shí)代》所提醒的那種狀況。在人工智能的時(shí)期,或許我們可以更果斷地界說(shuō)人道:甚么是人道?人道是那永久沒(méi)法被人工智能所替換的部門。